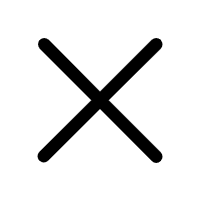摘 要: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赋应该算是汉代的代表性文学形式了,关于汉赋的艺术特色以及它的讽刺功能,众学者对他们已经做过了很深入的研究,我这里就不做重复性的工作了。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述一下汉赋的讽刺和娱乐功能之间的微妙关系,汉赋的讽谏和娱乐功能在一开始就是兼而有之的,并且娱乐的成分还要多一些。
关键词:汉赋 讽刺功能 娱乐功能
说赋这种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学形式一点儿都不夸张,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也有提及汉赋的篇数,“进御之赋千有余首”,班固在《两都赋序》中的说法是,“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要比同一时期的诗歌的数量多出好多来,《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差不多是同时期诗歌数量的三倍,这只是西汉时期的大致数量,到了东汉,辞赋的数量更多。而上述西汉作品的数量估计也是他们搜集的一个略数,所以汉赋的数量还要比们说的多一些。
汉代辞赋何以如此的发达,这种盛况就如唐诗,宋词一样,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和时代,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以及辞赋这种文体本身功能上是有着很深的关系的。中国自古至今都有一个士这一阶层存在,这一阶层的人大多数都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思想,在其人生的追求当中渗透着立功这样的一种思想,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士,皆不例外。但是总有很多士人是不得志的,要想跻身朝廷与皇帝议论国事,并不是谁都可以的,这除了个人要有真本事以外,还有待于一种机会。文士可以写文章议论朝政,但是要想达于皇帝之耳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汉武帝却给这群想以辞赋进身之士带来了这样的机会,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有这样的一则材料: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赋奏,天子以为郎。
汉武帝如此的欣赏司马相如的辞赋或许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单纯爱好,因为辞赋本身铺张扬厉的文风,使人读了都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一介寒士司马相如的因赋得官很清楚的表明了武帝对辞赋以及辞赋作者的一种态度,那时辞赋作者就有了一个入朝议政的一个渠道,当时文人定当效仿,一时之间,作者蜂起,作品迭出“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 ;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自此以后辞赋已经可以和朝政与仕宦之路联系起来了,这种关系的建立,在推动辞赋发展的同时,肯定会促使人们对辞赋自身价值定位的思考,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司马迁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的意思是,辞赋的价值定位应该是“讽谏”,而那些靡丽之词和虚词滥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只要不影响辞赋发挥它的“讽谏”的功能的话,也无甚大碍。
然而被司马相如扬雄,以及后来的司马迁看作是对帝王讽谏作品的赋作,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能改变汉代帝王的原有的意志,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如在《汉书·司马相如传》和《汉书·扬雄传》中都有关于扬雄给武帝上《大人赋》的事情,《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鉅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腥,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
相如意在“非帝王之仙意”,有“讽谏”之志,然云“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也流露出迎合武帝“尚靡”的心理,知其好而迎合之。《大人赋》描写仙界奇幻、倘恍,鬼谷、幽都阴森恐怖,惊险刺激,又可满足皇帝猎奇之心,因而具备了娱乐功能。其《上林赋》,山川、风物、乐舞、畋猎无所不包,精雕细镂,穷形尽相。山川风物之富有,乐舞败猎之气势,映射出汉帝国之气象,作品本身之美感,之气势,就发人情志,歌功颂德之意已寓于言中,相形之下,当他们完全沉迷在这种审美的体验当中的时候,“曲终奏雅”式的讽谏之意便蔽于华采之下了。辞赋最初讽谏的定位对讽谏的对象没有起到丝毫的效果,反而是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赋这种文体的特点直接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赋体的创作特色是,用大量的篇幅来铺陈所描写的事物和张扬事态,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总结的那样“赋者,铺也。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品物毕图”极尽铺陈之能事去描写和刻画事物,以西汉大赋最为明显。它们或极言宫苑的规模宏大,或描写汉帝国物产的丰富繁多,或刻画武士的刚毅威猛,并在这些描写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运用想象的手法,并把自己的感情倾注进去,辞赋的这些特点使它具有的审美特点高于它的讽谏功能的,这也难怪帝王们读了之后,会被这种及其艳丽的文风所吸引。当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感叹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中审美的眼光去欣赏的,得到的自然仅仅是艺术上的感动,并没有体会到文章当中的那委婉讽谏的意思。从这点来推测,汉武帝本来就是从娱乐的角度来看待司马相如的辞赋的。
当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无论是高居庙堂的统治者,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山野村夫,都有一种优越感,整个社会都弥漫这一种强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以铺张扬厉的文风为特征的辞赋正好可以凸显汉帝国的威势和优越性,令观者产生一种敬仰和敬畏的心理。“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承秦制后,汉帝国的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这种极尽渲染之能事的铺描就是向世人炫耀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的绝好手段。这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体在精神上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力和盛大的气象,同时也赞扬了皇权的强大和神圣,起到了“润色鸿业”的作用,并以此证明皇权的神圣性。这种文体正好迎合了汉帝国皇帝的对自己建立的功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自然是欣喜有加,而那些想以辞赋为进身之阶的文人们也就投其所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之间的这种有意无意的配合,更是发挥了汉赋的娱乐功能。扬雄把赋这种铺陈描写多,而讽谏委婉而少的特点总结为“劝百讽一”,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驰骋郑魏之声,曲终而奏雅”。他对这样的“劝”太多,而“讽”太少的辞赋创作表现出了不满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他后期对辞赋的态度,称作辞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汉书?扬雄传》说“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髭、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复不为。”《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扬雄一直希望辞赋能发挥出政治效用并期待着凭此效用使个人的身份地位得到提升,但是他这种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种观念和汉帝国的皇帝根本的意识中所持的娱乐态度相背离的。辞赋不仅不能对皇帝起到劝谏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娱乐的工具,于是扬雄便“不复为”了。
汉代辞赋的娱乐功能不仅表现在群臣文士那他们去娱乐帝王,他们之间也以辞赋互相娱乐,《西京杂记》载鲁恭王得文木,中山王作赋令“恭王大悦,顾盼生笑,赐骏马二匹”,恭王、中山王虽各为诸侯王与朝廷臣僚不同,但身份相类。二王之赋乐则为共娱,是纯粹戏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定位是“讽谏”的汉赋,但讽喻宗旨难以左右君主们的意志情趣却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它实际收到的效果和本来的目的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是带着娱情的眼光去欣赏辞赋的。汉赋讽谏的本来目的没有达到,却获得了娱乐这一功能。其实汉赋本身写作特点决定了他的审美功能是多于实用功能的,这也就决定了它自身的娱乐功能是大于讽谏功能的。
参考文献:
[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
[2] 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月。
[3]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
作者简介:敬晓愚(1983.2-),女,四川南充人,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基础部助教,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汉赋的讽刺和娱乐功能 汉赋
来源:职场范文网 时间:2019-03-30 04:58:50